原標(biāo)題:一次對“曠野寫作”價值的重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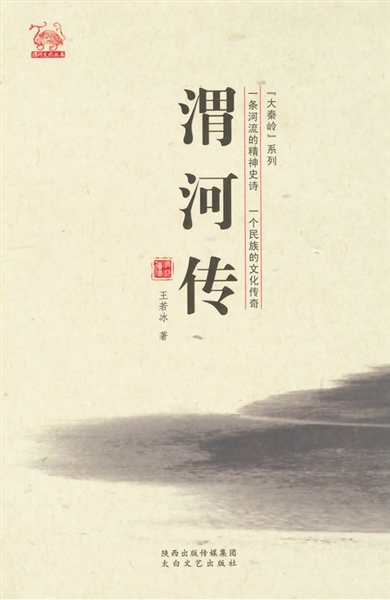
《渭河傳》王若冰著 太白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王若冰甘肅天水人。詩人,作家,秦嶺文化學(xué)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天水市文聯(lián)副主席,天水日報社副總編,天水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甘肅省宣傳文化系統(tǒng)“四個一批”人才。出版、主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十余部。主要作品有詩集《巨大的冬天》,“大秦嶺”系列《走進大秦嶺》《尋找大秦帝國》《渭河傳》《仰望太白山》,電視紀(jì)錄片《大秦嶺》等。
從2004年肇始,王若冰為自己確立了“一座山,一個民族,兩條河流”的宏大寫作計劃。一座山指秦嶺,一個民族指秦人,兩條河流指渭河及漢江。落實到文本層面,它們依次對應(yīng)的是《走進大秦嶺》、《尋找大秦帝國》、《渭河傳》以及行將完成的《漢江筆記》。
《渭河傳》出版于2013年底,2014年4月第2次印刷,這也是王若冰孕育時間最長的一本書。今年3月12日,在西北師范大學(xué)舉辦的《渭河傳》研討會,再一次讓王若冰以及這本書走進讀者的視域。
2011年8月中旬,在一輛借來的紅色“獵豹”的馬達聲中,王若冰關(guān)于“集中而完整考察渭河流域”的行程終于得以動身。彼時,微博和微信都還沒有流行起來,從他博客圖文推送的“直播”中,我們經(jīng)常看到的一個固定形象是:在一條泥濘的路上,身著被汗水打濕的短袖衫,肩挎巨大的相機包,手握一瓶礦泉水,泥水從鞋底翻卷上來漫過鞋面,眼睛圓睜如負軛的牛……這便是路途中的王若冰。讓人不禁想起西部詩人昌耀筆下“一個挑戰(zhàn)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盤”的情狀。
“由于多年來對渭河的關(guān)注與思考,這次渭河之行,我側(cè)重于以一種持續(xù)完整的行走與觸摸感受古老渭河在我精神和內(nèi)心所呈現(xiàn)的狀態(tài),而不僅僅是俯視與探尋。為了整體呈現(xiàn)渭河古老博大的歷史文化精神,我跑遍了甘肅、陜西、寧夏三省區(qū),包括十?dāng)?shù)條支流流經(jīng)的渭河流域廣大區(qū)域;我也查閱了沿途各縣區(qū)的志書,走訪了還遺留著渭河古老情感經(jīng)歷的村鎮(zhèn)古道、歷史遺跡,并從多達數(shù)百萬字計的文史資料里,尋覓渭河留在中國數(shù)千上萬年歷史中的古老回聲。”《渭河傳》后記中,王若冰如是說。
故此,作家馬步升認為,王若冰的散文是“走出來的”。“由于散文這種文體本身邊界的模糊性,是否敢于對邊界地段展開突破,是否真的有所突破,突破幅度的大小,這種突破是否具有文體的、認識的、美學(xué)的價值,正好成為檢驗一個散文家的考場。王若冰自覺地給自己設(shè)計了這樣一組考題,他也模范地完成了這種自我測試,從而實現(xiàn)了自我超越。這一切,根源于他的不懈行走,和行走中的苦心思考。”這種打破散文約定邊界、“泥沙俱下”的寫作,在研討會上,王若冰的同鄉(xiāng)、詩人張晨稱其為“全要素寫作”。
一定程度上,王若冰的行走不僅僅是資料收集的過程,還在于對自己書齋經(jīng)驗的一次重審與印證。或許,只有當(dāng)渭河沿岸的泥土緊粘于腳底,在滯重的步幅中,他才真正找到了敘述的自信,才抵達了自我理想寫作狀態(tài)的秘境。批評家謝有順曾提出“曠野寫作”的命題,他說,曠野寫作就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天空和大地,在大地上行走,接受天道人心的規(guī)約和審問。
照此而言,王若冰包括《渭河傳》在內(nèi)的“大秦嶺”系列的書寫,無疑是對曠野寫作向度及價值的一次回應(yīng)和重申,盡管這種回應(yīng)可能不是出于批評家的理論指引,它更多來自王若冰自我寫作困境的突圍與文化自覺的召喚。
經(jīng)歷了對渭河流域幾乎全景式考察后,王若冰承認,“面對和秦嶺一樣沉智偉大的渭河來說,愈是對她非凡身世關(guān)注久了、思考深了,就愈覺得她負載的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精神和文化情感過于古老、凝重、豐富多彩;以我原有的線性思路,如果順著渭河干流流向從渭源縣鳥鼠山到渭南潼關(guān)走下去,是不足以發(fā)現(xiàn)并理解渭河古老凝重、豐富遼闊的精神世界的。”
王若冰:渭河既是我言說的對象,也是表達我體認的喻體
蘭州晨報:你是以詩人的面目被讀者知曉的。在此次研討會上,評論家唐翰存認為“大秦嶺”系列的書寫拯救了你的寫作,至少在寫作方向上如此。你是否認同?可否簡要回顧一下你與秦嶺文化結(jié)緣的前前后后?
王若冰:翰存的發(fā)言可謂一語中的。我寫詩很早,持續(xù)而激情的詩歌寫作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達到高潮,也在國內(nèi)詩壇浪得一點虛名。同時,我是一個習(xí)慣反思反省的人,應(yīng)該是在我迄今唯一一本詩集《巨大的冬天》出版前,我就在思考自己原有寫作的方式、價值和意義——我總覺得開始于八十年代的極端個人化寫作難以承擔(dān)這個裂變時代的精神情感,我必須尋找一種更為宏大的精神文化背景,開拓自己寫作新視野。到了上世紀(jì)九十年代后期,這種想法愈來愈強烈,為了調(diào)整這種焦灼、迷惘情緒,我有意識放緩了詩歌寫作速度,更多地投情于原本我就熟悉并自覺另有滋味的評論、散文寫作。直到2004年,莽莽秦嶺突然浮現(xiàn)在我面前,我苦苦尋覓了將近十年的彷徨之路才豁然一亮。接下來的情況關(guān)注我的讀者都知道,在《走進大秦嶺》出版和以《走進大秦嶺》為藍本的八集紀(jì)錄片《大秦嶺》播出后,不僅“秦嶺是中華民族父親山”概念迅速得以普及,秦嶺旅游熱和秦嶺文化研究熱潮一夜之間走紅并且持續(xù)至今,我的寫作視野也豁然開朗、寫作天地更加遼闊。所以翰存說“大秦嶺”系列拯救了我的寫作一點不為過。因為從完成《走進大秦嶺》后我就發(fā)現(xiàn),我很幸運地找到了適合我、可供我享用一生的寫作天地。
蘭州晨報:在網(wǎng)絡(luò)資訊發(fā)達的今天,一些資料完全可以坐在書齋得到,當(dāng)初為何決意要選擇“行走”甚至“苦旅”的方式親身走一遍?這樣的親歷是否改變了你最初的寫作構(gòu)想?
王若冰:事實上,持續(xù)十多年秦嶺南北的行走寫作,改變并豐富了的不僅是我的寫作本身,還有我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態(tài)度。對于寫作來說,最明顯的莫過于進入秦嶺之前,我為自己將來完成的作品取好的書名是《秦嶺批評》——一看書名就明白,當(dāng)時我試圖延續(xù)盛行于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文學(xué)”余響,借助秦嶺反思并批判傳統(tǒng)及傳統(tǒng)文化。然而進入秦嶺后,我所看到、聽到、觸摸到的一切卻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調(diào)整思路。最后的結(jié)果是,腳踏實地的行走與親歷,讓我從大秦嶺的批判者一夜之間轉(zhuǎn)為大秦嶺的膜拜者、歌頌者。
蘭州晨報:我們注意到,《渭河傳》一書始終有“我”這個第一稱的介入,但在渭河畔長大的你自始至終沒有提及自己有關(guān)的童年記憶,而這一經(jīng)驗往往是作家們慣用的方式。是否因為類似的個體經(jīng)驗與本書的宏大敘事之間難以平衡?或者出于其他考量?
王若冰:說我在渭河邊上長大其實并不準(zhǔn)確,因為我老家在渭河南岸山上,要真正感受雨季到來渭河濁浪滾滾的壯觀,還要趕十幾公里山路。“大秦嶺”系列寫作主旨本來就定位在給高山河流立傳并以借此探尋我們民族文化精神根源上,這樣的大題材往往在時空上要穿越上下幾萬年,我不可能面對一座見證一個民族興衰沉浮的文化圣山和一條負載了一個民族滄桑史的河流抒發(fā)自己一己之幽怨的。這幾本書里我所急于訴說的,是我對一條河流、一座山脈、一個族群文明史的認知和思考,所以更多的時候我需要有意識克制自己的個體情感——即便如此,讀者還是不難發(fā)現(xiàn),我掩飾不住的情感時不時會噴薄而出。至于行文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我”,既表明我的寫作姿態(tài)——那就是我是在行走中寫作,更是為了強調(diào)現(xiàn)場感,即作者與讀者同時在場。
蘭州晨報:在本書最后一節(jié)《遠去的鄉(xiāng)土》,你筆鋒急轉(zhuǎn),落腳于現(xiàn)實關(guān)懷的層面。可以理解成“卒章顯志”嗎?換言之,這是否是你為渭河立傳的初衷?
王若冰:是的。《渭河傳》寫作初始我就確定了借助渭河滄桑千秋變遷,映現(xiàn)中國農(nóng)耕文明由盛而衰歷史過程主題。渭河的變遷史亦即中華民族的滄桑史,渭河既是我言說的對象,也是表達我體味與認知的喻體。面對宋明以后渭河流域自然生態(tài)日趨惡化,以渭河文明為標(biāo)志的中國古代農(nóng)耕文明日漸式微的歷史,面對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城市化步伐正勢不可擋地將維系一個民族精神血脈的鄉(xiāng)土精神徹底摧毀的現(xiàn)實,隱痛、惆悵、彌望幾乎伴隨著《渭河傳》后期寫作全過程,既是為了“卒章顯志”,更是為了傾訴對鄉(xiāng)土中國依依難舍的懷戀之情,才有了原本沒有計劃在寫作提綱之內(nèi)的《遠去的鄉(xiāng)土》。
蘭州晨報:目前,你對漢江流域的考察是否完成?有沒有相應(yīng)的寫作計劃?
王若冰:對漢江的考察已經(jīng)于2014年分兩次完成,《漢江筆記》的寫作已經(jīng)開始。《漢江筆記》是“大秦嶺三部曲”的最后一本,由于單位工作十分具體、壓力非常大,只能利用節(jié)假日擠時間寫作,進度非常慢,但無論如何我得在年內(nèi)完成。《漢江筆記》完成后,它將和《走進大秦嶺》、《渭河傳》共同組成我12年來不舍晝夜、苦苦經(jīng)營的“大秦嶺三部曲”。
文/蘭州晨報 記者 張海龍



已有0人發(fā)表了評論